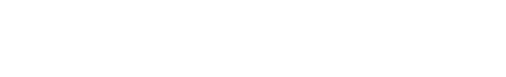内容提要:在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进行的既有学术批判中,兼容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是一种方法论革新,从时间观的反思、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机制化理解、重视多重因果链等角度,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中对民族国家的设定进行了多维的解构与重构,从而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维度和视野,对我们认知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因其越来越无法合理而透彻地诠解国际政治现实,日益遭到东西方学者的诟病。在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理论范式的批判和拓展中,兼容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社会学路径,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执拗低音”。历史社会学路径的研究者们,其批判的维度与拓展的议题虽然呈现出相对驳杂的局面,致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系列的历史社会学”[1]21,但当我们仔细审视既有的历史社会学著述,抽丝剥茧地进行整体梳理后就会发现,这些著述从不同的维度上解构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民族国家的理论假设,从方法论层面进行了革新,对我们批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思考重构国际关系史叙事和重构国际关系叙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历史学强调时间序列,社会学强调社会结构,“历史社会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2]。历史社会学方法介入国际关系研究,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的时间差异、空间重叠、多因果链等问题重新纳入了考量视野。但这种综合思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渊源有自。
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者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社会学,往往愿意称之为“回归”,原因在于历史社会学方法介入国际关系研究并不是新近出现的事物。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曾强调,自己在1954年的《法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就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到20世纪50年代末,受到雷蒙·阿隆影响的斯坦利·霍夫曼则提出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借鉴历史社会学思路。[3]
1962年,雷蒙·阿隆在其颇为得意的《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尤其是来源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启发,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提出了批判。比如,他强调国际关系研究要对所认定的行为主体进行反思,“不能将国家一词视为法国大革命以后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4]5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应该也包括希腊城邦、罗马帝国、欧洲君主国等。在分析国家行为时也要考虑到,“国家针对彼此的行为并不仅仅由力量关系所控制:观念和情感影响行为体的决策”[4]96。可以说,后来建构主义、英国学派所提及的观念、文化、情感等因素,雷蒙·阿隆在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中已经注意到了,但却没有引起当时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学界的重视。这一点雷蒙·阿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无感伤地提到,虽然这本书在法国得到了高度赞誉,但“这些评价,不管怎样可贵,却反映不出此书在美国受到的待遇”,因为在美国同行看来这本书竟然胆敢在国际关系领域创造“理论”。[5]573
此后,在美国学界的主导下,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历史社会学路径的研究和反思,思想上的光芒被持续遮掩了。今天被学者们频繁提到的创作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社会学著述,只是在冷战终结之后才被大量讨论,获得了应有的荣光。可以说,是冷战的终结引起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真正的集体性反思。无论是国际关系的现实议题研究,还是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用于寻获规律、洞察时局,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种国际政治大变局的出现却出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的预判。一些新现实主义理论家曾强调两极格局在结构层面的超稳定性,结果两极格局突然崩塌,历史走向了新局面。这种新局面势必会对学界的思考产生巨大冲击。冷战终结,形成了一次新的历史分水岭,“随着历史的加速,这种分水岭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出现。我们目睹了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被重构,边界被重新划分,联盟被重新调整,新的身份出现了,旧的忠诚也被恢复”[6]。如何认识这种复杂的历史转变呢?兼容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社会学路径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今天,在一系列对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进行综述的文章中,列出了长长一串为历史社会学路径做出贡献的学者名单。这些学者包括但不限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雷乌斯-斯密特(Chris Reus-Smit)、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耶尔·弗格森(Yale H.Ferguson)、亨瑞克·斯布鲁特(Hendrik Spruyt)、约翰·霍尔(John Hall)、托尼·贾维斯(Tony Jarvis)、斯蒂芬·霍布登(Stephen Hobden)、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马丁·肖(Martin Shaw)、米歇尔·巴纳特(Michael Barnett)、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巴里·布赞(Barry Buzan)、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约翰·鲁杰(John Ruggie)、巴里·吉尔斯(Barry K.Gills)、克莱尔·卡特勒(A.Claire Cutler)、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肯·布思(Ken Booth)、理查德·曼斯巴奇(Richard W.Mansbach)、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甚至还包括以研究民族主义著称的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以研究全球市民社会为主要志业的简·斯科尔特(Jan Scholte)等。通过审视这样长长一串学者名单,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些学者来自多个研究领域,拥有不同的研究偏好,而且有些学者并没有直接从事过国际关系研究,他们只是在各自具体议题的研究中为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为使分属不同研究领域、拥有不同研究偏好的学者能够在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上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斯蒂芬·霍布登和约翰·霍布森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2002年,他们两位主编论文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社会学》,力邀自觉从历史社会学视角思考国际关系的学者,分别从自己的研究专长进行撰文,产生了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些受邀撰文的学者包括斯蒂芬·霍布登、约翰·霍布森、马丁·肖、米歇尔·巴纳特、雷乌斯-斯密特、巴里·吉尔斯、安德鲁·林克莱特、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巴里·吉尔斯、克莱尔·卡特勒、史蒂夫·史密斯和弗雷德·哈利迪。为了使我们对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的认知更为条理分明约翰·霍布森还在该论文集里撰文,将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细分出了七种研究路径,分别是:1)新韦伯主义历史社会学(Neo-Weberian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迈克尔·曼、安东尼·吉登斯、西达·斯考切波、查尔斯·蒂利;2)建构主义历史社会学(Constructivist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雷乌斯-斯密特、约翰·霍布森;世界体系历史社会学(World Systems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巴里·吉尔斯;4)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Crit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t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安德鲁·林克莱特;5)批判历史社会学(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安德鲁·林克莱特;6)后现代历史社会学(Postmodern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史蒂夫·史密斯;7)结构现实主义历史社会学(Structural Realist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7]20-41
霍布森的分类看似清晰无碍,实际上也存在问题。一方面,这七种细分研究路径未必能够将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全部涵盖,比如有学者指出“文明分析”也是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之一。[8]另一方面,这一分类也可以直观地看出其模糊性,比如安德鲁·林克莱特既被霍布森看成了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也被看成了批判历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
对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进行梳理时出现的人物众多、派系驳杂、归类不清等状况,都指向了同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当作为一种方法的时候,前人的著述不免成为启迪后人思想的来源,因而一些学者也就不免被强行纳入历史社会学研究阵营。如乔治·劳森以建构主义历史社会学为例,指出这一派历史社会学研究重新发现和拓展了埃米尔·涂尔干、卡尔·马克思、安东尼·葛兰西和马克斯·韦伯的一些思考,同时受到了晚近的安东尼·吉登斯、于尔根·哈贝马斯和欧文·戈夫曼等人作品的影响。[9]而安东尼·吉登斯正是一些学者在梳理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时反复提到的学者。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虽被看成为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要么在著述中未必有着充分的向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拓展的自觉;要么只是在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对既有国际关系研究展开了反思,并没有形成系统性认知。因而我们会发现,在历史社会学阵营中也存在学者之间的相互批判。如霍布森认为斯考切波虽然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对历史社会学方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批评说“每当她讨论国家间的关系时,这些关系总是被毫无例外地理解为冲突”[7]72。再比如,新韦伯主义历史社会学虽然看到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引入了多因果链的思考,但仍然被批判过分注重物质而忽略了身份、文化等因素。
总体来看,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存在着分别聚焦、无法形成统一理论框架的问题,历史社会学学者们对此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如克莱尔·卡特勒直言,“历史社会学没有办法提供像新现实主义那样的国家理论”[7]184。历史社会学学者之间的学术旨趣不同,又使得他们虽然可以被归类在历史社会学阵营,但他们之间的思想和理论张力也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史蒂夫·史密斯就曾明确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社会学“面临着身份危机”[7]223。但需要为历史社会学进行辩护的是,能否形成严密而精致的理论不应成为评判一种研究路径优劣的标准。因为建构理论的目的并不在于完成智力游戏,理论建构的初衷是为了认知复杂世界。所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社会学反思即便是方法而非理论,也对我们在时局的演变中洞察国际政治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但面对流派纷呈、议题广泛、聚焦不同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我们的确需要寻找到一条主线来较为清晰地认知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做出的贡献。本文寻找的这条主线是历史社会学研究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中民族国家设定的多维解构与重构。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遭受诟病最多的一点,是其一直以静态、停滞的方式认知国际政治结构,缺乏对流变和转型的深入思考。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雷蒙·阿隆早就批判过的,即假定所有国家都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形成的民族国家,并将这些民族国家假定成同质的,它们不仅具有同样的对国际政治权益的衡量,而且应该具有同样的行为模式。这种假定以先验的方式去除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立论的根基实际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而形成这种叙事的根本性问题所在,在历史社会学学者看来是时间观问题。
历史社会学学者认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预设了一种时间观,霍布森借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说法,对这种时间观进行过精当的批评,称其为“时间拜物教”(chronofetishism),这种时间观对时间进行了现世主义设定。[7]5在现世主义设定之下,现实国际政治中发生的问题只需要从现实中寻找答案即可,拒绝从历史流变入手思考问题。与之相反,历史社会学研究就是要引入历史维度,重新思考时间,通过时间观的改变而解构民族国家同质化的设定。
综合来看,目前既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对时间的反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将时间重新类型化。在这方面,本雅明、布罗代尔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启迪。本雅明在自己的哲学思考中不仅考虑了时间的量度,还考虑了时间的类型。一旦把时间类型化,思维的开阔性也就呈现出来。金伯利·哈钦斯指出:“本雅明所讲的时钟时间(clock time)与历史发展的线性、确定性、不可逆和空洞的时间相联系。这样,按照牛顿物理学的术语来讲,政治行为(乃至革命)都可以被解释为由物质所决定的。本雅明所讲的日历时间(calendar time)与时钟时间不同。日历有起止点,日期也会出现重复,但重复的日期并不是一个平淡无奇时间点,而是回想与创造,是时间的重塑。”[10]71-72布罗代尔则在自己的历史学研究中,尤其是在其代表性著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对时间进行了长时段、中时段、短时间的划分,分别属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事件(个体)时间。[11]在本雅明、布罗代尔等学者的启发下,在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对时间类型化进行深入研究的是约翰·鲁杰。鲁杰认为时间既在物理形式上产生流变,对应寒来暑往、季节轮替,同时时间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影响我们的社会认知。鲁杰把时间区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增量时间(incremental time)、结合性时间(conjunctural time)和划时代时间(epochal time)。为了使三个相对晦涩的概念便于理解,鲁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增量时间是把社会中的时间分割成无限细分的离散单位,事件之间因而不具有确切的连续性。以人口问题为例,鲁杰认为从增量时间角度来看,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人口属性(主要指年龄、性别、健康程度、民族构成、空间分布等)与竞争对手间的差别。结合性时间关注的是时间周期,在时间周期内,一个事件与同时而生的其他事件形成结合效应。以人口问题为例,典型例证是美国战后的“婴儿潮”。“婴儿潮”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与其直接关联的美国人口规模的变动,它还影响了住房、学校、就业、交通、消费品的需求和供应以及文化景观、犯罪率和党派政治等。划时代时间则被鲁杰看作类似于历史学家强调的长时段,划时代时间是一种对结构性变化的衡量。以人口问题为例,划时代时间衡量的是长时段中一个具体社会人口承载能力的结构性变化。[12]156-158把鲁杰的思路扩展开来,把时间类型化之后我们会发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民族国家同质化的设定是沉浸于增量时间之中,而结合性时间和划时代时间并没有被认真对待。
其二,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跨时空对比的批判。一旦聚焦到时间观念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立论中的跨时空对比就引起了历史社会学学者的批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原本已经因为现世主义取向,将同质化的民族国家设定为立论根基,但在具体的论证中又经常将现代民族国家与前现代的城邦、帝国这种完全异质化的行为体进行脱域的时空对比。巴里·布赞等人指出,因为忽视历史流变,造成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偶尔考虑到世界历史时,最常采用的做法是从现在的角度考虑过去。因为这样做,论述就变得相对容易了。例如他们将希腊城邦体系中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冲突,或者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冲突,视为美国与苏联之间冷战斗争的类似物”[13]51。此外,经常出现的情形还有,把美国的当下行为与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进行对比。再比如,认为不同历史时期中大国之间的战争根源都是由相同因素诱发的。这种叙事导致与时间相关的因素被忽略了。这就不仅将现在的国际政治简化成同质化的民族国家的舞台,还将历史上的城邦、帝国假想成了与民族国家是同质化的。这造成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很难被对个案有深度了解的历史学家所接受。针对这一问题,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发展了历史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最显著的标志是它将时间性放在首要位置,认为事件的时间和顺序决定着政治进程。[14]对于历史制度主义者来说,关注政治事件发生的时间和顺序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塑造人类互动的多种制度中,政治参与者受到的束缚和所面临的机遇会发生演变,会推动形成不同类型的政治游戏及其规则。比如政治参与者对利害关系的理解会因时代而不同,国家所具备的实力会伴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而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因而历史制度主义者愿意关注确定时间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和具有制度变革意义的时间节点,这些都是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忽视的。考虑到历史制度的差异,我们也会发现由现代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和由雅典、斯巴达等城邦构成的希腊社会具有鲜明的差异,不能进行简单的脱域对比;同样的道理,美国与历史上的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也不能进行简单的脱域对比。
其三,对国际体系时间长度的拓展。对国际体系时间长度的拓展,重点在于对前现代国际体系的引入,也就是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之前的国际体系纳入国际关系思考之中。这种对前现代的引入不是历史学式的还原历史本身或重述过去,而是作为重新建构的起点,目的在于重置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在这方面,打破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研究起点的叙事至关重要。在打破“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束缚方面,结构现实主义历史社会学学者,或者更为人熟知的说法是英国学派学者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将“国际”关系扩展到超过5000年的历史中,将国际体系分析的起点放置在3500年前。“当时苏美尔的城邦国家在构成现在伊拉克一部分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区域里开始相互发生关系”,并给出结论“城邦国家构成了第一个已知的完全国际体系”。[15]1与这种观点类似,安东尼·吉登斯也曾明确指出,从欧洲历史经验来看,“国际”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国家主权的形成并不先于欧洲国家体系的发展,也不先于国家体系向全球的扩展”[16]263。当“国际”先于而不是迟于民族国家构建的维度被展现出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根基进行的“国际”关系议程的设定就可以被重构。
其四,通过对民族国家演进中不确定性的研究,打破对民族国家核心要素的先验设定,从而丰富时间维度。现代民族国家具备的一些核心要素被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假定为无须论证的存在,比如它具备的国族团结、民主架构、科层制特征等;还比如它是西欧中世纪封建模式的替代者和进步模式。针对前者,查尔斯·蒂利在其一系列著述中曾指出过欧洲民族国家演进历史中不同思想的竞争性、演进的不确定性等。[17]针对后者,亨瑞克·斯布鲁特提醒我们注意,在中世纪晚期,法国式主权国家、德意志汉萨同盟、意大利城邦并存,它们都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制的颠覆者和继承者。[18]一些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原则,诸如签订协议、确保协议的可维持性、确保均势,在汉萨同盟和意大利城邦都表现出来了,最后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综合导致法国模式胜出,后来法国模式在法国大革命后又发展成民族国家模式,这种民族国家模式才传遍全球。具体关注到当今的国际政治现实,一些国家也只是披上了民族国家的外衣,部族政治等前现代因素依然对民族国家模式形成挑战,这也就证明物理时间节点上的同一性并不代表着历史进程上的同一性。
历史社会学学者,除了从时间观上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进行批判,解构了其现世主义假定和民族国家同质化假定,也针对与民族国家直接相关的议题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是学界的集体动向。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共同市场,全球化推动的相互依存度提升以及人员跨境流动增多,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主要重视国家的视角存在明显不足,因而把非国家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比如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被看成是关于主权国家的第一次争论。入江昭的《全球共同体》就较早地对国家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了重点关注。但是这种研究方式,仍旧没有改变对民族国家属性的看法,关于国际组织的研究只是民族国家研究的延伸,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对跨社会联系的关注,各个国家的内部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旧被看成彼此离散的单元。
历史社会学学者的目标指向之一是要打通民族国家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以实证的理由争辩说,国内和国际领域的分化是一种现代现象。”[19]历史社会学家指出,国内和国际领域的分离并不符合现实,而是被人为建构的结果。换言之,这是一种叙事造就的印象,真实的国内和国际领域应该是一种内外交叠(overlapping)状态。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是联结在一起的,是国内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上的疏离,使对二者的研究形成了叙事上的差别。弗雷德·哈利迪指出,在没有参考一系列国际因素的情况下,不可能解释个别国家的政治。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国际”并不是“外面的”东西。国际社会经常会通过诸如炸弹袭击、油价高涨等形式侵入国内政治的政策领域。[20]20此外,如前文所述,国际关系是先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在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国际因素一直是重要的形塑力量。国家间竞争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原因和发展的方向,而国内资源的调动和使用则是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争衡的手段。
考虑到对国内和国际不该进行人为的叙事剥离之外,历史社会学学者还认真反思了如何认知国家的性质。这方面的反思是历史社会学研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共同贡献,被称之为“第二次主权国家争论”[21]1-14。查尔斯·蒂利、斯考切波这些主要精力并未放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之所以会被看成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社会学路径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在于他们在对国家性质的判定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学者发展了国家的理念,将其看成是声称控制某一特定领土的一组机制。”[1]20安东尼·吉登斯在谈写作《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的宗旨时也说,目标是“将民族国家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机制模式”[16]34。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对国家的定义是基于领土的,而历史社会学对国家的定义则是基于机制的,这是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的重要创见。
在历史社会学学者看来,不同国家的机制也并不是同质的。以斯考切波为例,在其名篇《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中,虽然探讨的是社会革命问题,但其在总结部分却探讨了国家的差异,认为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社会革命,“大都发生在落后于竞争对手的农业国家中,而非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并且设想如果社会革命发生在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那将是一场与历史上重大的社会革命迥然不同的革命”。[22]349-350斯考切波本身对于革命论题的观点是否具有说服力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种以历史重大事件为切入点的议题将国家的差异性点了出来。
相较于斯考切波将国家理解为社会机制、强调国际机制的差异性,迈克尔·曼思考的更多。迈克尔·曼转变了传统上所认为的社会从属于国家的状态,实现了从国家中心主义向社会中心主义转变。在其《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文版序言中,迈克尔·曼点明了自己的首要论点,“各个社会及其发展都是社会权力四种来源的产物。这四种来源是指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权力。政治权力也通过地缘政治延伸到国际领域,即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23]中文版前言1。在对四种权力来源的衡量中,与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将军事和政治紧密绑定不同,迈克尔·曼明确将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认为许多现代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没能有效控制国家内部的军事力量,同时有些国家的安全是依靠其他大国来维护的。更进一步,迈克尔·曼又认为人类的互动是置身于四种社会权力形成的可以区分的互动网络之中的,这样又在一定程度上以社会机制取代了国家机制,将视野拓展得更宽。
当把社会也理解为机制时,社会机制与民族国家边界的关系也就进入了历史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视野。传统分析模式中的社会边界以国家主权边界为边界,已经不再行得通。一方面,社会机制的边界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的边界重合,这方面部族主义国家为明显例证。在非洲等地区的部族主义国家,国家内部各部族的部族主义认同可以超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各个部族有自己的组织模式,部族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这成为这类国家内部治理的重要难题。另一方面,如约翰·鲁杰所说,“机制性体系未必需要固定的地理边界”[24]。鲁杰所举的实证性例子是历史上的蒙古游牧部落。尽管这种不限定明晰地域范围的游牧部落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游牧部落活动范围已经不能突破各自民族国家边界,但鲁杰的观点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比如现在的大型跨国公司,每个跨国公司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拥有自身机制的社会,它们具有历史上蒙古游牧部落的特征,并且对国际关系正产生着深远影响。
通过把国家和社会界定为机制,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可以跨越民族国家这一屏障,在一种或几种机制中建立联系,这样在认识论上也形成了复杂性思维。历史社会学中的一些著述还尝试“解释现代世界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和国际体系相互作用的结果”[25]119,也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以机制入手解读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尝试。此外,以机制入手认知国际政治还可以像詹姆斯·罗西瑙等人那样把视角进一步转换。当假想同质化的民族国家之间在无政府状态中博弈时,国家的思维自然是利益思维、囚徒困境思维,但如果换成以机制性视角思考问题,以全球性机制为思考重心,就能像罗西瑙那样对“没有政府的治理”进行探讨。[26]引入机制性思考之后,历史社会学学者们将国际关系研究“从静态的、简易的方法引向一种更为活跃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很好地理解社会行为和社会变化的动态性”[9]405。
历史社会学学者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的研究取向时,另一重要努力方向是强调多重因果链。当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或是追求简化、清晰的结构阐释,或是追求以某一框架或模型来表述主题时,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则对简化甚至单一因果链阐释方法提出了批评并重新引入了复杂性。比如,历史社会学学者们重点关注了重大社会政治变革对国际关系的意义,在他们看来,“社会政治变革只能通过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来理解,任何一种力量都不能被归结为决定性的单一本质”[27]。上文所提及的历史社会学著述中尝试从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和国际体系相互作用来解读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是一种多重因果链的展现。
在多重因果链视角下,民族国家的现世主义设定被淡化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得到了探讨。前文提及的民族主义研究著名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之所以被归为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的一员,就在于他对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过程进行了重点研究。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大众教育等因素在盖尔纳那里都得到了关注。[28]其他历史社会学学者虽然对民族主义意识生成、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认识,但无疑都采用了多重因果链视角。如巴里·吉尔斯虽然特别突出了资本在这种世界历史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但也强调要从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综合判断资本的社会效应。[7]159-161
从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着眼,尤其衡量到民族国家建构之前的国际关系状态,还有助于通过引入历史复杂性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无政府状态假定进行批判。多位历史社会学学者反复指出,欧洲中世纪的国际制度是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度的混合体;东亚朝贡体系的国际制度是以等级制为重心,同时行为体间并没有确定的权力依附关系,等级制更多地表现于文化和理念层面。此外,通过既有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无政府状态所占的时间比重截至目前并不比等级制所占的比重更长。由此,历史社会学学者强调,“无政府状态在历史上一直是不稳定的,不能被视为先验的假设”[19]345。当我们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只是国际结构属性的一种时,还可以把流变性引入到对无政府状态的思考,也就是要认识到“无政府状态的结构属性可以发生转变”[13]46,无政府状态有可能走入新的等级制状态或是其他模式。
多重因果链视角的引入,还扩大了国际政治研究的议题,并且使议题呈现出了更丰富的讨论空间。比如在对国际组织进行思考时,一些历史社会学学者认为,欧盟、联合国难民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队等多种国际组织不应被视为国家的延伸,这些组织不是“国家的女仆;相反,它们可以是富有创造力、充满活力和独立的实体”[7]113。将这种思考进一步拓展,个别学者甚至将这类全球性机构看成是形成全球国家(global state)的要素。虽然全球国家不一定能够真正形成,但马丁·肖认为,“这些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合法性,并作为一种类国家形态在全球范围内调节着经济、社会和政治”[29]。理念、信仰等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的因素,也被纳入了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视野。比如弗雷德·哈利迪指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对中东地区的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而问题背后,尤其对中东地区的误读,主要源于“对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的忽视,对国家内部和社会因素的严重忽视”等[30]25。
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在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维度上,还参与了对“人的安全”的探讨。冷战终结之后,“人的安全”概念提出并引发了相对广泛的讨论。人的安全,既是对普遍人权更泛化的阐释,也是对国际政治中新安全观的进一步延伸。“人的安全是安全概念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凸显了贫穷、疾病、环境压力、人权侵犯以及武装冲突等对人的安全和生存带来的危险。”[31]1那些推崇人的安全的论断,将民族国家边界置于次要的地位,以人本身的安全为终极诉求。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边界的存续是不利于人的安全实现的。“18、19世纪国家作为国际政治主角的地位得到巩固,安全也随之变得由国家来垄断。这一特点和过程首先在欧洲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得到强化和补充。民族主义作为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把国家及其主权与国家群体合并起来,这在较大程度上使个体身份掩盖在国家概念之下。”[32]8这类研究通过把人放置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位置,在努力突破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叙事模式,这种转变需要思考的问题更为复杂,所要阐释的层面更为多元,因而也只有多重因果链的思维模式才能够应对这样的议题。
当然,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引入的多重因果链,有些论断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叙事方式。比如,按照一些学者所论,全球化已经生发了一种资本逻辑,这种资本逻辑的特点是资本的运作与流动打破了民族国家领土边界的束缚,拥有了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是资本对于人来说是工具性的,不像民族国家认同一样是更为根本的身份定位和认同诉求。实践资本逻辑的典型是区域联盟或称区域共同体,但目前来看区域共同体并不能够消解民族国家身份,也难以真正消解民族国家边界。再比如对人的安全的探讨,从视角上具有革新意义,从理念上更具人道主义关怀,但更为实际的问题是,如果民族国家本身被判定为不值得信赖,那么由谁来确保人的安全?
虽然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会有自身的问题,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尤其是当我们发现前现代因素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仍然存有强劲的影响力时,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的确为我们审视和批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的不足提供了有益参考。总体而言,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为我们思考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尤其是在解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民族国家设定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构。历史社会学是一种强调历史流变性的研究路径,当历史还在流变,当旧的历史现象仍在反复,新的历史现象还将出现时,我们以一种动态的、不断重构的视野去审视国际政治、理解国际关系也就更加合乎情理和现实。(注释略)
文章来源:《151amjs澳金沙门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06期